筑牢法人治理根基
赋能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中)
作者:耿碧君律师
二、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痛点及典型案例
(一)社会团体
社会团体基于会员共同意愿组成,通过会费、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等维持运作,核心功能是 “会员利益代表”,治理结构依赖会员大会-理事会体系。
1、合规管理缺失与形式化治理
当前社会团体合规管理存在显著短板,其突出表现为对法定义务的履行缺位。这种系统性治理缺陷正严重制约着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具体而言,大量团体存在年检制度执行不力、基础登记信息长期未更新等问题,反映出法人治理结构已陷入"形同虚设"的治理危机。
(1)年检制度执行不力
2025年7月,广西民政厅对广西鲲鹏足球俱乐部等9家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原因皆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或提交年度工作报告”。这些组织涵盖体育、教育、商业等多个领域,包括足球俱乐部、电子竞技俱乐部、教育基金会乃至省级商会(如广西北京商会)。同样严峻的是,广东信宜市在2025年7月一次性对108家社会组织发出限期整改通知,原因均为未参加2024年度检查,清单中包括市篮球协会、游泳协会、房地产中介协会等本应活跃的组织。2025年初洛阳市对23家社会组织撤销登记,2025年6月黄冈市水上救生协会因连续两年未年检且登记证书过期被公告撤销,反映出合规意识淡漠已成为普遍现象。
(2)组织僵化服务缺位
福建省在清理“僵尸型”社会组织过程中发现,许多组织虽然登记在册,实则处于“名存实亡”状态——既无实质活动,也不履行注销程序。这些组织挤占行政资源,破坏行业生态,但因注销程序复杂、责任主体缺失而长期滞留。洛阳被撤销的23家组织中,“洛阳市工业强市研究会”、“洛阳市尊老爱幼促进会”等名称宏大的组织赫然在列,但其实际运作早已停滞。这一现象反映出社会团体在法人治理层面存在"宽进严出"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组织运行效率低下,治理效能难以提升。
2、非营利属性异化与财务失控
社会团体的核心特征在于其非营利属性,但现实中这一本质也面临严峻挑战。部分团体出现资产变相私有化、关联交易规避监管等乱象,使其沦为治理风险高发领域。财务管理的失序不仅逾越法律红线,更严重侵蚀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基础。
(1)财务制度失序
2021年深圳市某行业协会通过虚开发票、截留会费等方式设立"账外资金"累计87万元,用于发放福利、宴请等。财务凭证缺失,部分支出仅以手写白条入账。深圳市民政局调查后对该协会撤销登记,并将法定代表人列入失信名单,涉案5名责任人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2)自我造血能力不足引发的恶性循环
行业协会商会一定程度上存在“等靠要”思维,资金渠道单一,过度依赖会费收入。这种财务脆弱性倒逼两类畸形生存策略:一部分组织通过强制入会、高额收费维持运转;另一部分则沦为行政附庸,接受政府摊派任务换取资源。
3、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与决策失灵
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空壳化"问题,主要表现为决策机制失灵和权力监督失效。当理事会只是走过场、换届选举变成争权夺利的工具时,这种表面化的治理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更导致了组织治理合法性的根本性危机。
(1)决策机构虚置化
北京市某研究会“一言堂决策”,理事会沦为盖章工具:近三年所有决议文件均无讨论记录,仅附理事签名页(后证实部分签名系代签);重大事项未审议,单笔支出80万元的办公楼装修项目,未经理事会讨论,直接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实施。被市民政局对研究会“警告”处罚,限期补开理事会追溯审议。并强制要求今后会议记录需包含“反对意见记载”。
(2)换届程序表面化
河南省某书法家协会理事会长期不履职,协会连续3年未召开理事会,重大事项均由会长个人决定。2023年换届时未提前公示候选人、未召开会员大会,仅由5名常务理事“内部投票”产生新班子。被民政厅宣布换届结果无效,责令重新选举,原会长因“长期不履行民主程序”被列入社会组织失信名单。
4、行政历史依附与权力寻租
我国社会组织的现代化治理改革一直面临着"行政依赖"的深层制约,这一问题在行业协会商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推行了机构脱钩等改革措施,但实际运行中仍然难以摆脱惯性,导致治理转型流于形式。
(1)中国某协会“红顶中介”案,协会8名专职工作人员中6名为借调公务员,违规使用行政机关办公室;以“行业标准认证”名义向企业变相审批收费,未开具发票,资金流向不明。被民政部警告并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清退借调人员,并对涉事公务员进行问责。
(2)东部某市餐饮协会“摊派敛财”事件,市场监管局要求餐饮企业“自愿”加入协会,否则“重点检查”。协会向企业出售“食品安全示范单位”牌匾(2万元/块),资金用于监管部门“联谊支出”。经调查,市场监管局局长被免职,协会注销登记。
当前社会团体法人治理存在的问题已超出局部调整的范畴,必须通过制度重构、技术升级和文化培育等系统性改革来解决。诸多负面案例反映出,现有法律体系不完善、治理理念不成熟、制度缺失等问题亟待解决。
(二)基金会
基金会以捐赠财产从事公益事业,扮演 “资金中介” 角色,治理核心是确保捐赠资产保值增值和公益目的实现,具有严格的理事会-监事会制衡结构。作为公益慈善的核心载体,其法人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社会信任体系的稳固。近年来频发的负面案例暴露出我国基金会在财产管理、内部治理、外部监管及历史遗留问题上存在种种缺陷。
1、财产管理失效与非营利属性异化
(1)慈善资金违规运作
2025年7月审计署报告披露,晋江市慈善总会向地方融资平台“晋江城投集团”出借10亿元善款,用于政府投资项目。这笔资金占该机构22年总筹款额(47.54亿元)的21%,且类似操作已持续5年——2020年前借款11.105亿元,2023年起年报中“借款”变为“委托”。违反《慈善法》核心原则,慈善财产必须全部用于慈善目的,禁止挪用或向企业借款,合法投资应分散风险,而非集中借给单一债务高危企业;且晋江城投无金融许可证,不具备受托理财资格,年报“委托”涉嫌虚假陈述。
(2)资金管理透明度不足
尽管《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已实施多年,但部分基金会年报仍流于形式。2024年某教育基金会因未披露关联方交易被处罚的案例中,其年度报告显示公益支出占比达70%,细查却发现近半资金流向理事会成员亲属控股的服务商。这种“自我交易”不仅违反《慈善法》禁止性规定,更导致捐赠财产变相私有化。
2、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与决策失灵
(1)决策机制虚置化
晋江案例中,10亿元资金拆借未经理事会实质性审议,仅以“讨论资金使用”的模糊记录搪塞。
这种重大决策绕过治理机构的现象并非孤例,2023年某扶贫基金会为追求高收益,将60%资产投入私募股权基金,恰逢股市震荡导致本金亏损40%。追责时发现,投资决策仅由三位理事闭门敲定,既无投资委员会专业评估,也未履行重大事项披露义务。
(2)监管缺位
儿慈会案中,内部监事未发现或未能制止前受助人柯某孝私自以项目名义诈骗患儿家长近千万元,暴露监督彻底失灵。终被民政部停止活动三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将其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相关负责人被责令罢免,儿慈会副秘书长、9958项目负责人王某更是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关联交易与利益输送
(1)虚假投资、低价处置资产
河南某高校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同时担任校办企业法定代表人,由基金会接受校友捐赠的某科技公司股权(估值2000万元),半年后以“保值增值”为由,以1200万元低价转让给校办企业。转让未经第三方评估,校办企业次年以3800万元转售,差价2600万元流入校方“小金库”。被认定“基金会理事会未对交易合理性进行论证,未履行重大资产处置程序,变相输送利益。”理事长被党内警告,校办企业负责人免职。
(2)溢价采购
上海某社区基金会将“老年助餐”等项目以“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外包给秘书长亲属控股的社工机构,3年累计支付服务费680万元。调查发现,实际服务成本不足300万元,且部分服务由志愿者免费提供,差价被用于购买关联方理财产品。基金会账目显示“专家评审费”支出,但所谓“专家”实为秘书长配偶;外包合同约定“管理费比例40%”,远超行业标准。秘书长被开除公职,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司法。
4、信息披露不足与公信力崩塌
2012年11月8日,包商银行出资5000万元在民政部设立包商银行公益基金会。自2019年包商银行出现信用风险被接管后,该基金会发展陷入困境。2022年,该基金会因未按规定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被民政部警告并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2025年,包商银行公益基金会未上报2023、2024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相关规定,被作出拟吊销登记证书的行政处罚。
5、行政干预与旋转门腐败
某日报社原总编辑吴某雄退休后任基金会理事长,利用职务影响为关联企业承揽政府项目。资金异化为“小金库”,通过虚列调研费、咨询费等套取资金142万元,用于个人消费及利益输送。吴某雄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基金会登记证书被吊销。
(三)社会服务机构
社会服务机构作为提供社会服务的主力军,其法人治理逻辑与社会团体、基金会存在本质差异。其系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养老),以举办人捐赠、服务收入为主要资金来源,组织架构相对灵活。其核心特征是 “服务提供者” 角色。
社会服务机构的独特性在于其面临 “公益属性”与“市场生存”的双重张力—因直接面向市场收费,更易发生持续性、系统化的资产转移。这一矛盾成为其治理危机的根源。
1、非营利属性异化:社会服务机构财产权属模糊性易诱发资产私有化,表现为两类典型乱象:
(1)关联方利益输送
2022年某民政部门抽查中发现一起典型案件:某社会服务机构被关联单位无偿占用资金近100万元,且该重大事项完全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事件暴露后,民政部门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责令整改,经整改后虽收回款项,但暴露了社会服务机构财产被视作“可支配资源”的认知偏差。此类操作的本质是将社会服务机构异化为关联企业的“提款机”,彻底背离非营利属性。
(2)变相分红机制
部分社会服务机构负责人错误认为 “出资即股东”,通过三种方式变相侵占资产:高额薪酬:向创始人支付远超市场水平的工资;虚假借款:以“临时周转”名义长期无息占用机构资金;关联交易溢价:向关联企业高价采购服务。
此类行为在民办教育、养老机构中尤为普遍。
2、内部治理结构失效:社会服务机构的治理短板同样集中体现为 “理事会形式化”与“监督机制缺失”:
(1)决策程序虚置
北京某自闭症康复中心章程规定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2次会议,但实际 3年未召开正式会议,重大决策均由创始人(兼任理事长)单独决定。监事由创始人之妻担任,从未审核过财务账目。2022年机构挪用30万元捐赠款用于创始人个人购房,直至员工举报才曝光,终被吊销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创始人被列入社会组织信用信息“黑名单”。
(2)监督制衡机制缺失
成都某环保组织章程要求设2名监事,但实际空缺5年。在无监督情况下,接受高污染企业30万元“环保宣传赞助”,并为企业出具“绿色认证”虚假报告。被认定“内部治理完全失效,监事会形同虚设,沦为利益交换工具。”并取缔该组织,负责人被行政处罚。
3、财务管理制度缺位
(1)资金挪用
北京某养老院将政府发放的 200万元“床位改造补贴” 转入理事长个人账户,用于购买理财产品;通过虚报护工人数套取 50万元“运营补贴”(实际护工仅8人,申报25人)。财务由理事长亲属把控,无独立会计;理事会3年未审议财务报告。2023年被民政局撤销登记,理事长涉嫌诈骗罪被立案。
(2)账外资金
上海某儿童康复中心通过收取家长“现金赞助费”(不开具票据)设立 “账外资金”120万元,用于发放员工奖金、理事长海外旅游等。被内部员工举报,民政部门突击查账发现手工记账本。被处以吊销登记证书,退还家长费用,理事长列入社会组织失信名单。
(3)虚假支出
深圳某文化中心利用虚构的“兼职人员”名单,每月冒领工资补贴15万元,持续2年合计360万元,资金终通过现金取现方式转移。经审计比对社保记录发现“员工”均无参保信息。终被追回资金,法定代表人终身禁止担任社会组织负责人。
4、服务质量失控
(1)专业能力缺失
广州某养老院内 23名老人平均体重下降超10公斤,调查发现采购账目显示“食材支出”与实际用餐人数严重不符,每日餐标仅8元/人(合同承诺25元);护理员无证上岗,长期未给卧床老人翻身,导致7人患严重褥疮。后养老院关闭,家属集体诉讼索赔,法定代表人被禁止从业。
(2)安全隐患
深圳某残障康复中心使用过期3年的康复药物为残障人士治疗,导致多人不良反应;药品采购无记录,部分药物来源不明;机构无专职医务人员,理事长称“药物是捐赠的,未检查有效期”;理事会会议记录显示“全员通过”采购决议,但实际未召开会议。终机构被取缔,2名负责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被调查。
社会服务机构法人治理的危机,本质是财产权属模糊性与服务市场化张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痛点的化解需回归社会服务机构作为“服务型捐助法人”的本质——既要承认其通过服务收费维持生存的合理性,又需通过理事会制衡、关联交易管控、行业协同监管构筑非营利性防火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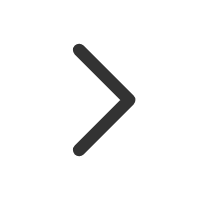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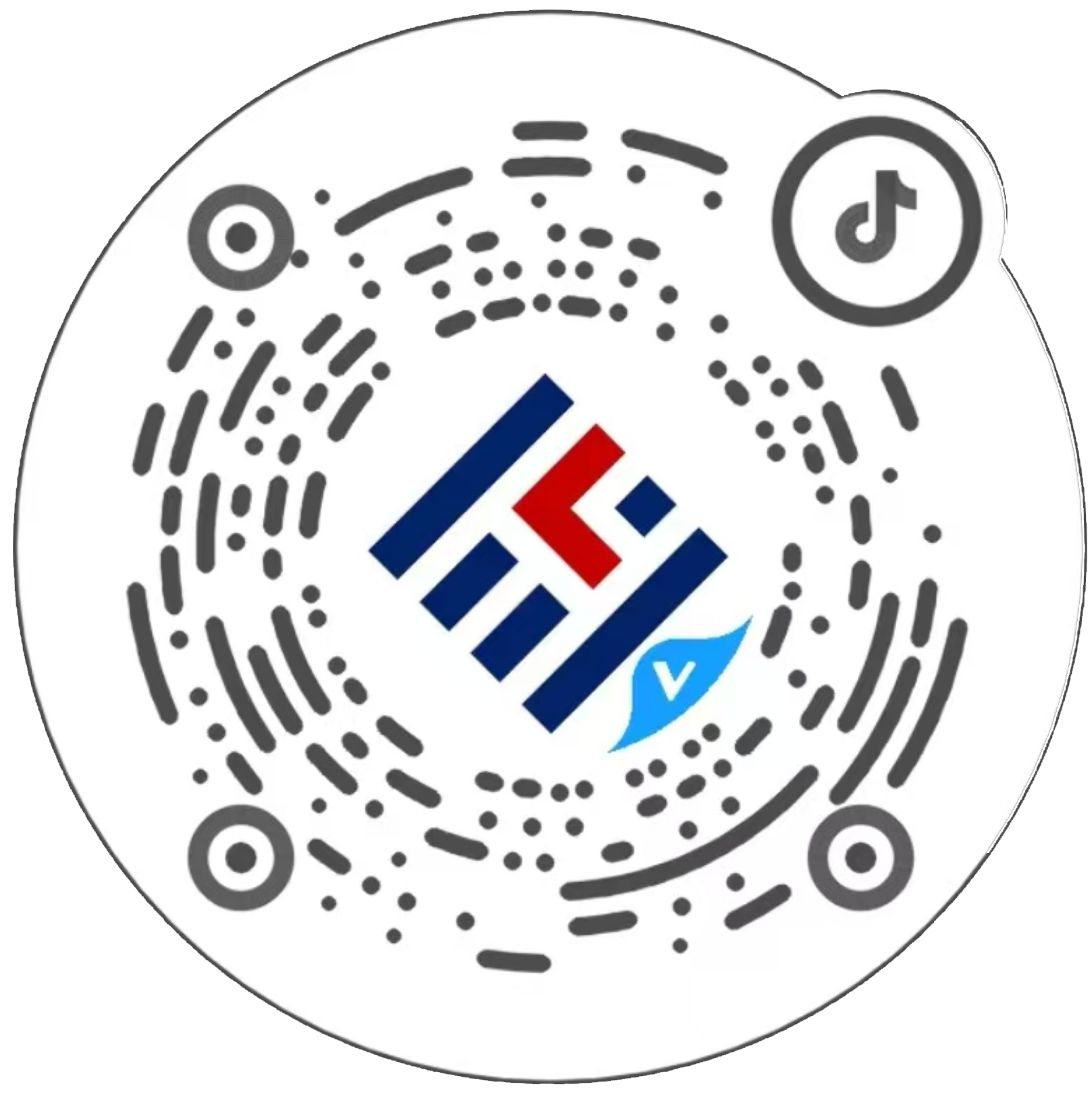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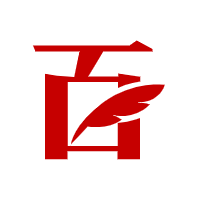
.png)
.png)







